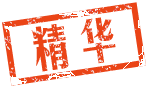|
梅镇是个不大然而却很出名的镇子,之所以出名,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镇上的那家“百花楼”。 其实“百花楼”不过是一家很普通的花坊,——说花坊那是雅称,说白了就是一家妓院。 “百花楼”的有名,全是因了海棠红。 海棠红是“百花楼”的头牌舞小姐。“百花楼”里群芳争艳,海棠红之所以独占鳌头,是因为她的确与众不同。其一,她人长得漂亮。那种漂亮不是胭脂水粉画出来的,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生丽质。不光是男人见了心生仰慕,就是同是女人的其他小姐,也暗暗称羡。其二,她有一身的好舞艺。镇上最有学问的白先生称其舞姿是“嫦娥转世,飞天再生。”据有幸观看过其舞的人称,看过她的舞,三日不思茶饭而不知饥渴。 据说海棠红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小姐,其父是东北军的一名军官,跟随少帅多年,后来不幸战死;其母一病不起,不久也撒手人寰。遭此不幸,很快便家道中落,海棠红辗转流落至此,万般无奈,找到了“百花楼”的花妈妈,投身做了舞小姐。那花妈妈看其出落得楚楚动人,又认文断字,自是心生怜爱,平素里也不怎么勉强她,自由她去;从此算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所在。 海棠红平日对姐妹们很好,常教她们识字唱曲,给她们讲一些书本上的故事,姐妹们都很喜欢她。海棠红对客人是有礼有节,温文有加,尽管她纤纤柔柔,奇怪的是那些孟浪之徒却对她不敢造次。 唯一和她来往密切的人是镇上学堂里的白先生。白先生读过几天洋书,是镇上最有学问的人。海棠红常和他把酒相对,诗词歌赋,天上人间,相谈甚欢。那白先生一表人才,风流倜傥,很让女人动心。姐妹们常拿他打趣她,说他俩是才子佳人,天造地设;她也不言语,只是垂了头低低地笑。 日子如流水一般波浪不兴地流走,直到有一天。 那一天,镇上突然响起了枪炮声和皮鞋的咔咔声,日本人来了。
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,镇子里就失去了往日的宁静。 日本人在镇子四角挖起了深深的壕沟,筑起了高高的炮楼。夜晚的时候,亮晃晃的探照灯扫过来扫过去,象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,将黑夜的静谧撕裂。 镇子里的高墙上都用白灰刷着“大东亚共荣”的标语,打远一看,象一排白森森的牙齿。家家户户都挂上了膏药旗,仿佛都开起了膏药店。 “百花楼”的门口也挂了一面,在风里无精打采地晃荡着,就象花妈妈的心情。 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,这“百花楼”的生意是日渐萧条。也难怪,这年头,命都难保,谁还有闲心赏花听曲儿? 该来的没来,这不该来的倒来了。 正月十五一大早儿,“百花楼”大门口儿忽然响起一阵嘈杂声。打杂的刘二开门一瞧,差点儿没背过气去。大门口赫然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鬼子兵,肩上一水儿明晃晃的刺刀,在清晨的日光里闪着森森的冷光。 镶着金牙大虾米似的翻译趾高气扬地走进门,将一张大红烫金的请柬扔给花妈妈。请柬上赫然写着:
大日本帝国皇军拟三日后举行“大东亚共荣联欢大会”,特邀请海棠红小姐及众小姐参加为盼!
宪兵第三联队少佐 青木一郎
众人未及反应过来,忽见那金牙翻译一个立正,一阵皮靴声响,打门外进来一个日本人。 这个鬼子很年轻,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,戴着雪白的手套,一张脸刮得铁青。看样子想必就是那个青木一郎了。 鬼子青木走进大厅,四下里看看,做了个手势,立马有几个鬼子抬了几口精美的箱子进来。 “这些”,鬼子青木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说道,“是皇军的一点心意,请收下!” 众人没有作声。 鬼子青木四下里打量着,忽然问道:“海棠红小姐在哪里?” 众人依然没有说话,花妈妈咳了一声,“太君,海棠她——,她不太舒服——” 青木的脸立刻阴沉了下来,空气有些紧张。 “我在这里。”一个沉静的声音响起,海棠红披着一件红色的外套出现在楼梯口。“客人请楼上说话。” 鬼子青木看了花妈妈一眼,大步走上楼去。
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,楼上没有一丝动静。 其间丫头小桔上去续了两次水,回来偷偷告诉大家,那鬼子和小姐两人不知在说些什么,那鬼子隔着茶几盘膝坐得笔直,一副规规矩矩的样子。 大概过了一炷香的功夫,楼上的门忽然打开了。众人急忙翘首望去,只见鬼子青木站在门口冲里面一个鞠躬,说了句“沙扬娜拉”,而后无声而去。 鬼子走了。 花妈妈拿着请柬哭丧着脸,一个劲儿念叨着,“老天爷,这该怎么办?” “什么怎么办?”秋菊大声说道,“不去!死也不去!!” “鬼子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,压根儿就没安好心!——咱姐妹就是鸡,也不能便宜那些黄鼠狼!” “那地方就是阎王殿,去了不死也得扒层皮!” “咱姐妹是卖的,可咱也是中国人啊!是卖也得卖给咱自个儿的爷们儿!不能让那些畜牲脏了咱!” “就是,要那样儿,死了都没脸进祖坟!” “反正左右都是死,这么死了倒落了个清白!” ………… 门声一响,海棠红出现在门口。 “海棠,你听见了吗?”花妈妈老泪纵横,“儿啊,咱不去啊!听妈的话,咱不能让那些龟孙子糟蹋!大不了,妈和你们一起死!反正这世道也活够了!!” 海棠红静静地看着她们,许久吐出两个字: “我去!” 说罢,头也不回地进屋了。临门的一瞬,她又说了一句: “我跟青木说过了,你们可以不去。” 一片寂静。 “呸!”许久,忽然有人吐了一口唾沫。 “呸呸!!”接着有人跟着吐起来,“真不要脸!”
白先生是黄昏时过来的,仿佛喝了不少酒,脚步踉跄着,一张白脸却铁青。 白先生大喊着要酒喝,不给他就骂人,从来没见他这样子喝酒,这样子骂人。 人们都远远地看着,没人敢过来劝他。 海棠红在他对面坐下,他仿佛没看到似的,连眼皮都没抬一下,自顾地喝着。海棠红也不言语,拿了酒杯,和他一杯一杯对着喝。 喝到第五杯的时候,白先生忽然手一抖,一杯酒有一半儿洒在了长衫上。 海棠红一把抓住了他握杯的手,静静地看着他。海棠红的眼里似乎有水在流,白先生的眼里仿佛有火在烧。 两人就这么相对注视着,无言,许久。 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。白先生慢慢从她手里抽出手来,忽然手腕一抖,剩下的酒如一阵疾雨般泼在了海棠红脸上。 “婊子!” 白先生冷冷丢下一句,摇晃着扬长而去。“怒发冲冠,凭栏处,潇潇雨歇……”远处传来他哭一般的歌声。 海棠红似乎抖动了一下,然而她却没有动。慢慢地,她端起了酒杯,一饮而尽。一颗大大的泪珠,慢慢划过面颊,滚落在酒里。
三天以后,海棠红去了炮楼。据说那天她打扮得美若天仙。 炮楼里灯火通明,照得半个镇子一片明晃晃的,隐隐可以听到喧哗的音乐声和嬉笑声。据说这次联欢,鬼子来了许多大官儿。 小镇上的人们在叹息,更多的在怒骂。 将近午夜时分,忽然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,整个小镇似乎都在晃动。人们惊讶地看到,炮楼那边儿一片火光熊熊,映得半个天空一片血红。 天明的时候,人们听说“百花楼”的舞女海棠红在跳舞的时候,引爆了藏在身上的手榴弹,当场炸死一片鬼子,其中有好几个大官儿,那个叫青木的鬼子被炸掉了一只胳膊。
据在炮楼里做饭的三胖子回忆,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: 那天海棠红跳了很多舞,她一刻不停地跳着,仿佛要把今生跳完似的。她还喝了不少酒,和那些大小鬼子轮番地喝,把他们灌得东倒西歪,她却越喝越来劲儿。她最后一个舞好像叫《满江红》,——那舞跳得!妈呀,那哪是人在跳舞,简直就是要把魂舞出来,舞上青天!!直舞得月亮都变了色,舞得风都变了调。把那些鬼子都看傻了。一个个舌头伸出多长,跟狗似的。只有那个叫青木的鬼子,始终沉着个脸。 小鬼子们越看越起劲儿,海棠红就招呼着他们一起跳。他们跟一群狼似的围着海棠红跳着扭着,一个个丑态百出。鬼子越围越多,就在这当儿,海棠红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。
镇子后面的青山下,新起了一个坟包。坟前立着一块碑,上面写着:
舞者 钟国红 之墓 愚友 白正舟 敬立
那只是一个衣冠冢。人们才知道,原来海棠红的真名叫钟国红。
不久以后的某一天,那个白先生也忽然失踪了,有人说他上山当了土匪,也有人说他投了八路。 每一个清明节,都会有一个独臂人在墓前上香烧纸,磕头行礼,行事甚为恭敬。奇怪的是,有人说那人居然很象那个叫青木的鬼子。 那座坟前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开满了鲜艳的海棠,远远看去,象一片鲜红鲜红的血。
|